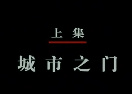在《新百姓》报战斗生活的回忆
史 明
1941年5月初,我跟随交通员从香港跨过深圳河,通过日本封锁线,抵达一个只有两户人家名叫新围仔的小村子,参加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在《新百姓》报社工作。
《新百姓》的创办者,是大队长兼宝安县工委书记王作尧同志。大家都记得,东江纵队的前身是曾生、王作尧同志的两个大队。1938年冬,日寇南侵,我党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争取国民党当局给的番号,在惠(阳)、东(莞)、宝(安)组建了曾、王两个大队。1940年3月,面临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一举包围歼灭的危急关头,东移去海陆丰地区,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党中央英明地指出,东移行动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军事上也必然失败,应返回惠东宝敌占区和国统区之间,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曾、王两部9月返抵宝安地区时,只剩下108人,由林平(尹林平)同志主持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上下坪会议,学习中央指示,总结经验教训,抛弃了国民党给的番号,脱掉了“合法”的外衣,部队改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曾部)、第五大队(王部)。主要力量编入第三大队,开赴东莞大岭山一带,王部留在宝安阳台山地区坚持斗争。经过大半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到1941年春,元气恢复,站稳脚跟,王部由30多人逐步发展扩大到二三百人,在建党建政等方面呈现蓬勃生机。事实证明,党的领导是胜利的保证,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王作尧同志“为了加强宣传群众和指导工作”(见《东纵一叶》145页)不失时机地决定办一份报纸,取名《新百姓》。
《新百姓》在王作尧亲自主持下,和他物色的李征等4人白手起家,于3月下旬办了起来,每周出一期,约200多份,第一期是8开4版。一版刊载国际国内时事,二三版报导地方新闻,四版是副刊。办报用的纸张、钢板、蜡纸、油墨由香港运回来。印刷技术是自己创造的,用木屐胶皮直接在蜡纸上刮,油印机不好用,又笨重,为了携带方便,钢板锯成两截,我们便成为一支“文化轻骑兵”。发行通讯网,由李征负责和交通站、税站、民运工作人员建立起来。
我到报社时,负责人是党小组长李征。杨奇和我是编辑,又是缮写员。还有老战士王培兴(王鸣)搞油印,我们几个人走到一起,说起来是有“缘份”的;李征原是马共产党员,在马六甲办过《工友报》,被英国殖民主义者逮捕,坐了四个月牢,1940年秋被递解出境,经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入部队。杨奇和我毕业于香港中国新闻学校(我是第一届,杨是第二届),是新闻出版界郭步陶、金仲华、乔冠华、刘思慕、张铁生等知名人士的学生。我在香港《申报》当过派报员,杨在《天文台半周评论报》当过校对。他和我又是“文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文艺通讯部)会员。他是《文艺青年》负责人之一,我在生活书店(后改名星群书店)协助《文艺青年》经销。1941年4月初,港英政治部便衣警探限令杨奇按时去“报到”,下旬几天之内,港英政治部的人到书店强带我去“问话”、“传讯”三次之多。为了免遭殖民当局的政治迫害,他和我经党组织安排,义无反顾地离开那个花红酒绿、人欲横流的“自由世界”,先后于四五月间来到《新百姓》报社。“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富有哲理的名言。刚到报社的日子,环境是极其艰苦的,至今记忆犹新。第五大队活动的地区,以阳台山为基地,东至布吉、水径,西至南头附近,是一条敌我犬牙交错的狭长地带,南面是“萝卜头”(日军)、“蕃薯兵”(伪军),北面是“呵呵鸡”(当地指瘟鸡,群众对国民党正规军杂牌军以此统称之),周围还有地主土豪武装和大股小股土匪出没。他们配合默契,与我为敌,我部队在两面受敌、三面夹攻的地带上,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流动性很大。报社也经常转移,什么时间、住在什么地方,很难记得清了。在新围仔,几个人白天在沙梨园草棚里编稿、排版、刻钢板、调油墨、印刷,有分工,又合作,满负荷地工作。尽管伙食标准定的每人每天一斤米、五钱油三钱盐,菜金一角,实际上经常不能达标。经济条件好时,每月加菜:鱼半斤、肉半斤。开始在邹义家搭伙,他为人热情,毕竟生活清贫,吃腌芥菜没有油,靠上面放一块肥肉蒸煮出一点油就是了。当年爱用一个比方,说中国是一块大肥肉,帝国主义列强都争着抢;现在许多人听起来会当作笑话,谁要大肥肉!我们只吃腌菜,舍不得用筷子动那块肥肉呢!主人让出放杂物的房间给我们睡觉,大家睡门板或打地铺,天气热,没蚊帐,挨蚊子的狂轰滥炸,盖上棉毯,又热又闷,喘不过气来。后来有了仅可罩住头部的蚊帐,身上盖毯子也很难忍受。免不了和香港比,城市里走的是平坦马路,这里羊肠小道坎坷不平,不容易一下子习惯。香港没有蚊子,这里苍蝇蚊虫防不胜防。“发冷”(疟疾)成了家常便饭。药品有一点,主要靠坚强的意志去对付,带病坚持。杨奇的病是三天五日流鼻血。7月间,我病得很重,大便都蹲不稳,是什么病也说不清。何婶来管生活,她给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后来我常说,没有何婶的照顾,我早已归天了。她几个子女参加了部从,加上其子何鼎华、何太、何通都是我们东莞中学先后同学,她以慈祥的母爱之情,把我从死神手里夺回来,令我深深地怀念。《新百姓》能坚持出版,应该说,她有一份功劳,至少也算苦劳。
《新百姓》在部队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依靠部队指战员和抗日爱国人士的支持,克服种种困难,在敌伪顽势力和反动舆论包围的环境中,建立一个舆论阵地,开辟一条新闻战线。根据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宣传党的政策主张,理直气壮,对日寇烧杀抢掠的血腥暴行,口诛笔伐,对汪伪卖国投降的面目,坚决揭露;对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无情抨击;对反动势力的造谣诬蔑,针锋相对;对抗日军民的愿望和要求,大声疾呼:对革命英雄事迹,热情赞颂;对愚昧落后现象,晓之以理。
总之,尽力把报纸办成党和人民的宣传阵地。四个版面,约1.6万字,我们在这有限的园地上,精耕细作,文字力求短少精悍、生动活泼、通俗易懂。但一文一字,对敌人,它是“匕首”、“投枪”,是“批判的武器”、“远射程的弹”;对人民,则倾注满腔热情,与父老乡亲和战友同呼吸,共命运。我们手上有真理,用事实说话,有说服力、吸引力、感召力,起到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报纸的内容,虽然现在难以详细回忆一一表达;即使后来与《大家团结》合并,仍定名为《新百姓》、《前进报》,办报的宗旨是贯彻始终的。
当然,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所限,我们也有缺点和失误。一是苏德战争爆发之初,我们根据香港一些报刊的提法,说帝国主义战争(德意日与英美法之间)和反法西斯战争(苏德)两种性质的战争同时并存,林平政委根据中央指示,及时批评纠正了。7月间,部队抓到两个“托派”,要我写一篇反托派的文章,我翻看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不外乎写托洛茨基派是列宁布尔什维克派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后来听说有的同志受嫌为托派,蒙了冤屈,倒没有听说有什么真正的托派分子。
约在7月中下旬,《新百姓》报社向东莞地区转移,经过宝安长圳时,得知目的地是东莞,我报请组织批准,把原姓名陈汝霖改为史明,这是我在香港《华商报》投稿被采用过的笔名(见1941年4月21 日《华商报》四版《一个女工的生活》)。俗语说:“好汉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难道我不当好汉?许多人参加革命后改掉带有陈旧含义的名字,采用单名。我考虑的,一是自己老家在东莞城郊梨川,家里有父母等七八人,我在香港时就知道,他们不断遭受汉奸土劣势力的欺诈,若被得知自己当了“老模”,家里的人怎么得了!二是我入部队时没有告诉在港的姐姐,也不让她告诉家里,因为有随时可能牺牲的准备,与其让他们日夜为我担惊受怕,不如让他们觉得我下落不明,抱着盼头好过些。直到1944年1月,我调任东莞大队任教导员时,回家探望,父母一见我,悲喜交集,泪流满脸,这是后话。出于这样的考虑,才改了姓名。再说,那时没有青史留芳、功成名就的念头,我写稿都随意用笔名,从不署真名,大概是“目光短浅”吧,也没想得很长远,牺牲了,胜利后家里会享受烈属待遇,幸存者,家里会挂个“参军光荣”的牌牌。一个永远写在个人历史上的日子,1941年8月9日,我宣誓入党:我在香港写了入党申请书,没来得及办好入党手续,我即入了部队,因转递费时,至此才举行入党仪式,当时,倍感“战地黄花分外香”。
《大家团结》是东莞地区第三大队创办于1941年的。两报于7月合并,仍为《新百姓》。一下子增加到十七八人。社长沙克(李廉东),支部书记金石坚,杜襟南被上级派来指导工作。杨奇和我以编写为主,李征为驻宝安特派员,何太负责东莞的新闻通讯,再加上其他同志齐心合力,可谓人才济济。中秋节前,“谭老板”(谭天度同志化装成商人而来,被称为“谭老板”一直迄今)、涂夫等人由粤北来了,使报社进入鼎盛时期。“谭老板”是1922 年入党的,有丰富的办报和革命斗争经验,对我们教育帮助很大。
这时,我们除了办报,又增加了一些出版文化课本、印制宣传品等任务,还做民运工作,中秋节当日正好日蚀,我们向群众宣传“天狗食日”的科普知识,开起晚会,真是热闹非凡,唱歌、讲故事、做游戏,一个接一个,新颖别致,充满情趣,今日的卡拉OK不一定能与之相比。郭际用客家话唱《游击队歌》,韵犹在耳。何太教会大家唱好几支歌,《八路军进行曲》“向前,向前……”
10月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保八团”、“挺进第六纵队”纠集反动地主和土匪武装共3000人,向我大岭山疯狂进攻,我军民奋起反击,战斗十分激烈,打了4天。报社也上了阿妈庙,出版几期16开四版用鲜红油墨印刷的《火线报》,专门报道反顽消息,鼓舞军民斗志。在紧张的战斗情况下,部队精简非战斗人员,有的分散去沦陷区掩蔽,有的暂时疏散回家。领导找我谈话两次,我坚决表示自己只能以革命为家,别无去路,才没被精简掉。
战斗结束后,报社改组。杜襟南、何太、涂夫等9人留东莞另有任务,沙克、金石坚、李征、杨奇和我等8人又返回宝安。到了白石龙,环境比较安定,报纸恢复正常出版,越办越好,发行量大增。特别要说一下刻字印刷技术方面,经过几个月的不断实践;有了很大进步。刻钢板、蜡纸上的黑格子不适用,买来的铁笔又嫌粗,我们用尺子在蜡纸上轻轻地划上线条,大体上竖90,横45,字体写成五号铅字大小。版面是竖排的,一个版面可容4000多字。刻字用留声机唱针,在钢板细纹面刻,笔划竖的顺力,横的就借助透明三角板很顺手,字体都写成长仿宋,标题除写成黑体、楷体、老宋体外,有的写成美术字。内容则分别不同栏目,画上小板头,加以美化,给人第一个印象是好的。游击区大多数是客家人,我们写小言论、编山歌,有时也适当用一点方言,如“唔得好死”(不得好死)、“个冇绝代”(断子绝孙)等等。
一个冬天的生活,天寒地冻,与其说靠一件薄棉衣、一条棉毯熬过来,不如说是靠年青的生命力和坚定的意志战胜的。草寮能躲雨不躲风。用竹片架成的通铺垫上厚厚的稻草,两人两条棉毯合起来孖铺,上面再加棉衣,脚下再加稻草,即使这样,仍常患感冒。难得有好天气冲个凉(洗澡)。大家都长虱子,得皮肤病,疥癣,甚至无名肿毒。有时经济困难或情况紧张,买稻谷自己推磨,于是就吃名副其实的“沙谷米”(本是洋西米之称)。有时吃蕃薯、芋头,别有一番滋味。轮流以津贴费买“巧克力”(片糖)、煮蕃薯糖水,或炒花生,是高水平享受了。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一大批名闻中外的文化人来到的日子。日军占领香港后,党中央指示部队配合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和南方工作委员会,不惜任何代价,把被困险境中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精英,从香港抢救出来。从1942年1月中旬起,几天之内,到白石龙来的不下千人。留下近百个文化精英,安顿在挨近我们报社小溪旁几间新草寮里。部队领导人林平、梁鸿钧、曾生、王作尧、杨康华亲自来接待。我们能与他们相处,实在千古难逢。茅盾、邹韬奋、胡绳、戈宝权……都是我们景仰已久的,邹韬奋是生活书店创办人。皖南事变后,国内生活书店50多个分支机构被查封或勒令停业,大批书店工作人员被逮捕或杀害,他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出走香港,一次我向他提及,他在港公布辞职抗议国民党反动政策的通电,是他要我刻钢板油印的,他觉得自己的店员参加革命武装斗争,献身于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引以为欣慰。他给我很大的勉励和鼓舞,过去,人们总认为文化人架子清高,但他们同我们保持着一种同志加师生的关系。我们多次请他们作报告,都欣然应允,但他们更喜欢以座谈会的形式,几个人一起向我们谈古论今,传授知识,有问有答,更显得亲切。
他们分批被护送往大后方,邹韬奋、戈宝权、胡绳、沈志远、刘清杨、沈兹九等二三十人同我们一起有两个多月。因为有人不慎引起山林大火,他们才转移到深坑,在深坑约为2月初,《新百姓》出版到三六期后,改名为《东江民报》。
改名是接受邹韬奋的建议。因为当时我们展出自己的报纸、小册子、教材、传单、歌曲等印刷品,邹韬奋、茅盾、胡风、宋之的等10余人看得很仔细,甚为赞叹,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邹韬奋认为以“民报”名义出现,更便于以人民的身份说话,冠以“东江”,突出地方特色。他的建议得到部队领导同志的赞同,他欣然挥毫写下了清秀隽丽的“东江民报”的报名(字体相当现在的《参考消息》大小),茅盾为副刊写了“民声”之名(字体如手表面大小)。为了表达对邹韬奋和茅盾的敬意,同时为了报纸以新的面貌出现,我想出一个办法,利用刻错或弄坏了的蜡纸,裁成长条状,刻写时细心描画,务勿走样,刻好就用小屐皮套印红色的。套红印刷,是始于此时也。后来,有的捷报和重要新闻,也如法套红。
据别人回忆,邹韬奋为《东江民报》创刊号撰写过社论,胡绳写过重要文章,杨刚写过反映欧洲战场的章回小说,丁聪画过漫画和插图。在他们的关心、帮助、指导下,报纸上还留下享誉国内外的知名人士的汗水和著述,如果人世间还能查找到,应该算得上珍贵的历史文物啊!
邹韬奋于1942年1月20日晨,特为曾生同志题写了“保卫祖国为民先锋”八个大字,并专为此写上:“曾生大队长以文士奋起领导爱国青年,组织游击队保卫祖国,驻军东江,韬从文化游击队自港转移阵地,承蒙卫护,不胜感激,敬书此奉赠,藉誌谢忱。”这对我们每一个指战员都是很大的鼓舞,并为之倍感荣幸。
《东江民报》出版了六期,因斗争形势的需要,改名《前进报》。金石坚、李征调出,留下杨奇等同志负责。我参加了初期筹办工作,4月底也和报社告别,到总队部警卫排做政治工作去了。
(作者是原东江纵队新生大队政治委员,离休前任福建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载《宝安党史通讯》第14期)
|
回忆录
在《新百姓》报战斗生活的回忆
https://dgds.sun0769.com 2009/1/21 10:37:00
编辑:刘韦玲